|
当代著名书家二十人系列评论之一 沈鹏 (沈鹏,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、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。) 沈鹏先生的大名,书坛上尽人皆知,即使是书坛以外,知道沈先生的人也并不少见,当然,这除了他以一手功力深厚,风格独特的草书令人折服之外,也与他担任着书坛乃至其他领域的重要职务有关。当然,由此也可看出沈鹏先生的社会影响之大。 草书发韧于西汉之初。卫恒在《四体书势》中曾道:“汉兴而有草书,不知作者姓名”。至汉武帝时,草书就已经在民间流行。我们从近代出土的汉简、汉墓砖上的文字可以得到验证。不过当时的草书在结构上还是依据隶书的形体,而将其写得急速潦草一些,所谓“解散隶体而粗书之”。后经杜操、索靖、皇象等人整理发展,经过了从“隶草”到“章草”、再到“今草”的数次演变。尤其是东汉的张芝,他将章草中带有隶意的波挑加以收敛,运用篆书中婉转回锋的笔法,使之气息流动,点画呼应,上下牵连,字之体势,一笔而成,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。故张怀瓘在其《书断》中说:“张芝变为今草,如流水速,拔茅连茹,上下牵连,或借上字之下,而为下字之上,奇形离合,数意兼包”。由于草书包含了所有书体的各种笔法,同时笔势飞动,务从简易,不易辩认,故不易学亦难精。而且从实用的角度来看,意义不大。但草书又是最易抒发个人情感的特殊书体,即使比较难学,但它还是以独特的魅力赢得人们的喜爱。 当代书坛,自毛泽东、林散之之后,尽管以草书擅名者并不乏人,但真正能在草书方面取得较高成就者,当属沈鹏。他的草书笔致厚重,奇崛苍茫,点画处理富于变化,既有传统经典草书的高古之气,又兼具现代生活的奔放跌宕的时代气息,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,人们面对沈先生的草书作品,即使掩上名款,亦能迅速知其出自沈先生之手,由此可见其风格之强烈。 凡习草书者,皆无一例外地要受到唐人草书的影响,沈鹏先生亦概莫能外。由于唐代是草书的成熟期,也是今草发展的颠峰时期,出现了张旭、怀素、孙过庭、智永等一批草书大家,尤其是张旭怀素的狂草,在书法已退出实用领域而其欣赏审美功能日见强化的当代,向上述大家借鉴取法,最易张扬书家的个性,故倍受人们青睐。沈先生于草法广取博收,以盘结奇气,丰富技法,但在结体上则于怀素《大草千字文》获益最多,尤其是那些纵笔(即长垂笔)的使用颇得怀素《大草千字文》用笔之妙。但他那些横撑的结体与用笔之法,则出之于他自己并不太成熟的“草隶”。但沈先生的草书当中,时时夹杂一些行书,尽管也以草书笔意出之,但在增加整幅开合起伏与疏密变化的对比效果的同时,也或多或少削弱了其草书的纯粹性,草书纯粹性的减弱,必然影响草书古意的精确表达,而这种草行搭配的写法,则又从中透示出一种现代人日趋复杂的人生情感。凡事有一得必有一失,以此观沈先生草书,应合此理。 沈先生为丰富和强化其草书的线条质量从而加强艺术感染力,大量地使用了颇具一波三折曲尽其妙的衄挫用笔之法,但此种笔法其实非沈鹏先生首创,此种笔法的始作俑者乃宋之黄庭坚,我们只要仔细品赏他的草书名作《太白忆旧游诗》便不难看出。而沈先生的创意在于他将这种笔法秩序化,并适当加强其草书线质的毛涩感,使其更加精致、细腻,从而化古为今,化他为我,将此形成自己的一种具有符号性意义的个情语言,写出了新意,写出了气魄,这是值得人们加以推重的。 沈先生的一些草书精彩之作,确实达到了“一画之间,变起伏于锋杪,一点之内,殊衄挫于毫端”的理想之境,殊非那些行笔直白外露一览无余者可比。但沈先生的一些作品也有因衄挫用笔过多而失之自然的地方,且有因擒纵失控而流于信笔之处。我想,以沈先生之学问功力,虽有此不足,但仍不失为一代草书大家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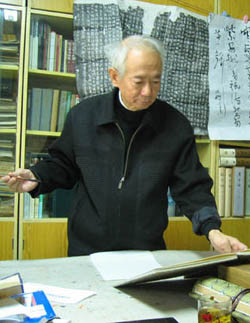
|